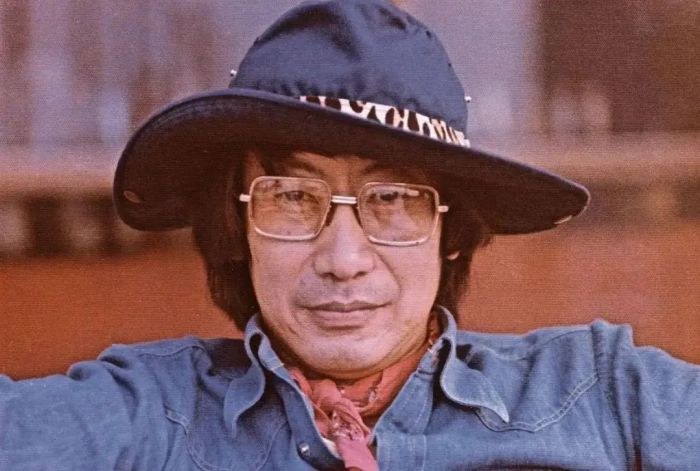姜文,一直被视为介于牛A和牛C之间的这么一号人物,之所以能有这个位置,并不是因为他拍了六部电影,部部让人啧啧称叹,而是因为姜文本人就在这个位置上。
所有的“姜文电影”,首先是“姜文”,其次才是“电影”。观众看一部“姜文电影”,电影里的姜文就像是“姜文电影”《邪不压正》里的李天然,不是一个人,是一支队伍,哪儿哪儿都是他。从电影院里走出来,被里面的荷尔蒙气息征服也好,被半路扔下不管的故事搞得云里雾里也好,观众总能获得一些复杂而又其妙的感受,一来不敢大声讲电影不好看,因为导演本人的地位,讲电影的不是只能证明观众自己不行;二来又会忍不住暗羡,中国电影市场大概只剩下姜文敢这么玩儿了,只有他敢这么任性,有这个本事甭管电影拍得怎么样,都够格处在那个牛A与牛C之间的位置上。

当下内地电影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类型,仍然是“联欢晚会”模式的,要么是有大场面,全明星阵容平铺直叙,万众欢歌庆盛世;要么类似小品的结构,先笑后泪总结升华,要切中民生社会问题,主题的向外延展性要强,在制造热点之余,为大众情感宣泄提供窗口,激发共情之后电影就红红火火了。
姜文电影显然不属于这一类。和晚会式电影相反,姜文电影不提供外延的可能,它只提供隐喻,角色身上多少能找到一点真实历史人物的影子,故事背后的历史并不严丝合缝地对应史实,但通过故事能够感知到导演本人的历史观,人物臧否也在其间。说白了,他只顾自己干自己的,压根不关心观众爽不爽,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,观众不介意票房就小扑,观众介意票房就直接扑街。
《邪不压正》成败与否,都是姜文的问题。电影里满眼都是姜文常用的意向,北京的屋顶、自行车、飞行中的凶器、枪、彰显女性性征的器官、双语使用者、穿插在其中的《带子雄狼》……当然,这几年里,最显眼的意向,可能还要数姜太太周韵。
这些姜文喜欢的意象被导演本人反复诉说,构成了姜文电影的风格中最重要的组成元素,它们被夹杂在介于现实和想象之间的时空里,时而和罂粟花田、牌坊似的师父塑像一起构成一种强烈的暗示,时而放空,用“姜文”这个概念把电影填满。
与电影里满满当当的修辞手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姜文电影构建故事内外逻辑的双重缺失,外部逻辑缺失导致《邪不压正》进入到中后程基本就在屋顶上直接起飞,让人搞不清这部分到底是男主角吸鸦片之后的幻觉,还是民国侠客江湖回光返照中颠覆常人理解的场景,故事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、意象化的展示。像西洋镜里头塞了“种田文”,许多细节值得反复玩味和推敲,可总体又假又虚,彼此缺乏连贯性。
内部逻辑缺失导致人物被虚化,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,在《邪不压正》里就是一个用来间接体现姜文男性荷尔蒙爆棚的“男花瓶”——光征服女人对姜文来说似乎已经没什么意思了,从《让子弹飞》开始,姜文就喜欢在电影里“玩弄”男性角色。彭于晏在电影里露胸、露屁股,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被窥视对象,“天赐大根”,天然的玩物。代表欲的唐凤仪(许晴饰)、代表念的关巧红(周韵饰)在姜文电影里不是花瓶,前者负责宣泄姜式荤段子黄话的嘴瘾,后者负责白月光式照明,“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”。红白玫瑰映衬出李天然这个空心角色的虚无。
缺乏内在逻辑的李天然一直在快速移动、疯狂地飘,被拍成了一个视角人物,负责向观众提供四合院房顶跑酷图景展示,并制造一些看上去硬条硬马实际上严重依赖后期的血腥场景。“天赐大根”的李天然乍一看特别像复仇故事的男主角,可他又被寄予了太多癫狂的浪漫主义的想象,并不苦大仇深,有一种真空中的天真,一轮轮寻根认父之后,变成了一个成长故事的主角,和圣·埃克絮里佩的“小王子”一样,驯养狐狸爱上带刺的玫瑰,最后还真抛出一句法语结语“塞拉为”(C’est la vie),这就是生活。姜文电影这样把观众按在地上任意蹂躏,这种粗暴的态度还真挺像生活的。
电影结束时可能半数观众头顶都能飘出四个肉眼可见的问号,“这就完事儿了?”疑惑程度和内心感受复杂程度,仅次于在《创造101》决赛舞台上,看到彭于晏和廖凡生无可恋地比出一个变了型的“心”。前期宣传跑得频,给人一种《邪不压正》票房压力很大的错觉,走进电影院发现姜文还是那个姜文,谁也不在乎,他只在乎自己,比其他电影人厉害的地方在于,姜文有本事展示“荷尔蒙爆棚硬汉文文”的妄想世界,用审视一种文化现象的心态去看《邪不压正》就很有意思,从电影的角度衡量姜文电影,用姜文自己的话说,就像“和太监做爱”。
收藏来源:百度澎湃新闻